|
转自2010年9月1日《东方早报》,作者石剑锋
日前,诺特博姆来到上海荷兰文化馆参加“阿姆斯特丹文学咖啡馆”系列活动,与中国作家毕飞宇对话,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。
 诺特博姆对自己的书有“不好看”的评价显然有些不服气
对中国读者来说,77岁的诺特博姆是一位略显陌生的作家。在世界文坛,诺特博姆是欧洲文学写作的代表,被美国人揶揄为典型的欧洲作家,换而言之就是“不好看”。可老头显然有些不服气:“我有一本书翻译成30种语言。”然后,诺特博姆很好奇地打听,他在中国的出版物质量如何,在读者中有什么反应,“在中国有书评写我的书吗?他们该寄给我,虽然我看不懂,但看看字也很开心。”记者说:“你的名字诺特博姆在中国读者那里太难记了。”“我的名字Nooteboom是核桃树的意思,对中国人来说,发音确实古怪。” 《万灵节》是塞斯·诺特博姆50年写作生涯中获奖最多的作品,老头也毫不避讳地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、最重要的小说。《万灵节》主人公阿瑟是个在柏林的荷兰摄影师,飞机失事他失去了妻儿,在柏林等待着去阿布哈兹做纪录片,反正哪里有灾难和死亡,他就去哪。所以,他以自己的方式看待所经历的历史。小说故事集中发生在阿瑟漫游柏林街头的30多个小时里。阿瑟像《尤利西斯》里的布鲁姆一样,在短时间里与一群哲学家、建筑师、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碰面,他们喝啤酒聊天,调侃德国历史,几乎没有情节。 谈东德,诺特博姆说:“一个独立的国家,夹在波兰和富裕的西德之间,想想看这是什么滋味吧!你难道想象不到那大规模的出走,那全面的解体?现在是西德为他们的梦想埋单,咬牙切齿地给他们埋单。”他又说东德人,“大部分人只是手气不好,拿了一手坏牌。他们既是受害者,又是帮凶,参与这样一个恐怖的误会,一个类似现实世界的误会:一个腐败的乌托邦。等钟摆摆向另外一边的时候,这乌托邦宣告结束。不变的只有痛苦,唯一不同的是,他们还得承受另外一半人的自高自大,而后者只不过是拿了一手好牌而已。”谈到两德统一,他借聊天调侃道,“他们觉得自己被忽悠了,谁能怪他们呢?开始我们张开双手,拿出一百马克大钞,欢迎他们,然后我们跑过去找我们的祖屋。把你的工厂卖给我们吧,我们更善于管理。……你可以把柏林墙拆了,但是这墙是不会消失的。” 塞斯·诺特博姆借着阿瑟与他朋友们的对话,来表达自己对德国统一和欧洲历史、未来的看法。这是一部思考性小说而不是情节小说,用作家自己的话说,“世上写故事的作家一大把,不缺我一个。” 我总生活在历史的时刻 “一本书写得过于复杂确实会丢失掉一些读者,但我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写到艺术家、哲学家这个复杂群体,那这本书肯定是复杂的。我不会为我的书难读而道歉。我不希望写一本很简单的书,但要是能写一本让读者绞尽脑汁的书,那也不错。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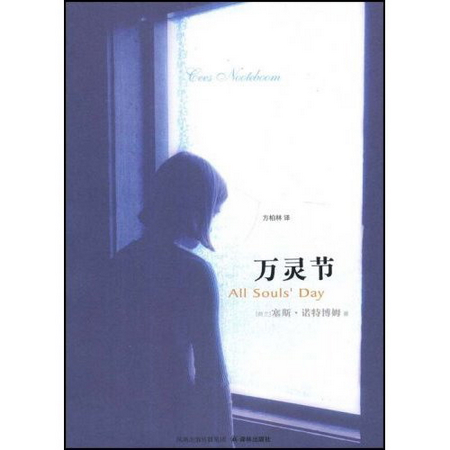 诺特博姆:我恰巧正在柏林,当时我受邀在柏林生活。那天我跟一个记者聊天,然后准备去餐馆吃饭,在出租车上,收音机里一片“嗡哇呀”声音,像是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情。我便问出租司机,司机是个女的,她说,“墙要倒了。” 我便说,“那载我们去那里。”就这样,柏林墙倒下的时候,我便站在那里,历史的时刻。这个情节我也写进了小说里。1956年我在匈牙利,见证了苏联的入侵。人们来问我,你说谁会来帮我们。我知道没人会来。战后,欧洲分成了两半,这块是你的,那块是我的,然后用严严实实的墙围起来。但是历史总是双重的,有开始就有结束。我目睹共产主义的兴起,然后是柏林墙倒了,一段历史终结。对我而言,这便是全部了。所以,我觉得,我总生活在历史的时刻。 我还有一本非虚构的书《柏林笔记》,逐日记录1989年,像写日记一样:专政推翻,统治者逃亡。德国人说,只有外人才会这样看那一年的德国,我们自己写不出来。英文版明年出。 早报:在《万灵节》里很多片段用来讽刺两德统一后一些荒诞的事,作为荷兰人你似乎对德国的统一有自己的牢骚。《万灵节》被看作是描写和反思两德统一的重要作品。 诺特博姆:我当时对有些德国朋友很失望。我原以为,他们这下可要开心了,你看,现在是一个国家了,不是更好吗?同一个民族,同样的语言又融合在一起了。可是,这些朋友抱怨为德国统一交税,他们不乐意了。 当时西德是什么,资本主义,有钱,好车;东德呢,墙推倒后,起初你去看的时候,真是穷得很,房子破敝。一夜之间资本主义来了,你得自个照顾自己。对普通人来说,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并不好过,可是资本主义也不容易混,说失业就失业了。正因为这些触动,我一定要写《万灵节》。你看,我们老了,只要人家不来干涉我们,别的什么我们都无所谓。 早报:你自己说《万灵节》不好读,很多人也抱怨你的小说很不好读,可是我感觉到小说充满着各种幽默。 诺特博姆:很多美国读者也说,这是一本欧洲作家的书,觉得过于麻烦。美国市场很难,太商业了,他们不喜欢我的书。一本书写得过于复杂确实会丢失掉一些读者,但我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写到艺术家、哲学家这个复杂群体,那这本书肯定是复杂的。我不会为我的书难读而道歉。我不希望写一本很简单的书,但要是能写一本让读者绞尽脑汁的书,那也不错。 关于幽默感,我非常同意。别人说我的这本书太严肃,我个人确实是很严肃的作家,但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,觉得很好笑,我知道不少德国人读《万灵节》时常常哄堂大笑。在这本书里,我借用小说人物开德国人玩笑。有人问我,为什么他读的时候就不觉得好笑呢。我说,词语在书里,幽默也在书里。 早报:你出生于1933年,成长于二战之中,那你会像格拉斯一样,写一本关于二战的书给自己吗? 诺特博姆:作为荷兰人,亲历了德国的侵略,我出生于1933年,1940年亲眼看到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德国人的军事基地,当时作为小孩子非常恐惧,我父亲反而是搬椅子出去像看戏一样,家里人要往我头上浇凉水我才能恢复理智。但我父亲后来不幸死于二战。欧洲总是有战争,但最不能接受的是有计划的对犹太人大屠杀,这是德国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问题,是必须接受承认的事实。 事实上,二战的时候我太年轻了,无法将之写成那样真正的自传。在现实生活中,我不是《万灵节》里那个摄像师,我的妻子也没有死,但我又确实出现在德国统一现场,这是我的成长经历。许多人说,你为什么不写这,不写那,可我最终只写出我以为对的东西。 此书豆瓣地址 |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